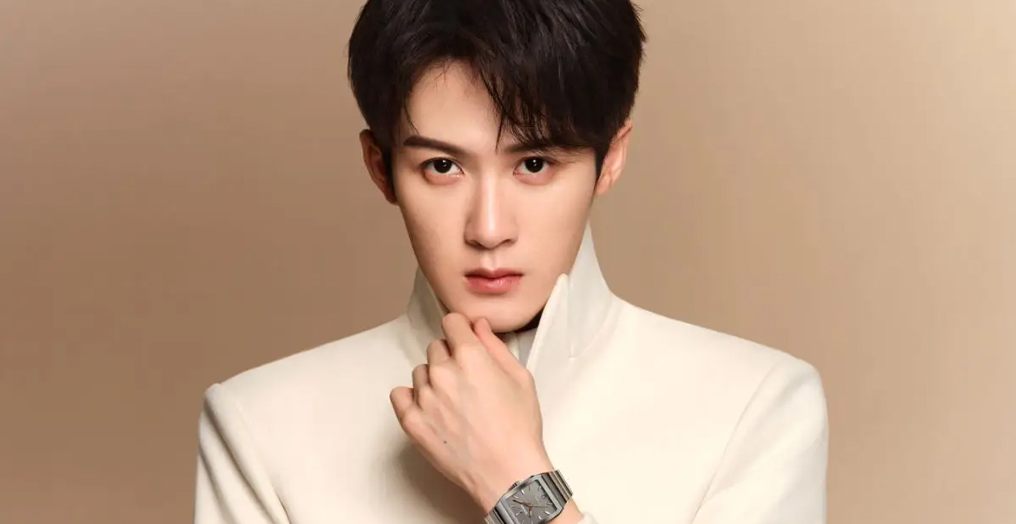《爱乐之城》是2017年第一部口碑引爆的电影,但就像很多以前的例子一样,物极必反,针对这部影片的各种批评声音终于还是慢慢发酵出来。
没有电影是免于批评的,《爱乐之城》当然也不例外。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我其实不太在乎立场本身。
下面这篇文章,是打算给支持这部电影的声音加一枚砝码,而且是重重的一枚。
作者是我们熟悉的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他在文章中也提到,争议性本身就是电影价值的重要部分。而他的核心观点是,《爱乐之城》在因袭传统的同时,也有很多创新。
本文是虹膜翻译组出品。希望加入虹膜翻译组请发信至whitevivi@qq.com。
作者:大卫·波德维尔
翻译:zhu yuqing、李大闪
校对:液化基顿、一生长眠
正统的方法极其简单,就是回归技艺。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1923
我想讲的并不是电影本身的制作。之后将会有DVD特别介绍《爱乐之城》的制作,现已有相关的幕后宣传片了。
这篇文章是关于《爱乐之城》是怎么拍出来的。
我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写影评,写自己爱的电影,或者说,至少是从历史或美学的角度上吸引我们的影片。有时候,我们感兴趣的也包含电影的争议性,比如说《爱乐之城》。
我的一些影迷朋友不喜欢《爱乐之城》。他们认为电影风格转换过快,从制片厂歌舞片转换到雅克·德米的风格,但同时又不遵从这两种模式。不过,口味是会变的。
我记得我们现在奉为经典的那些歌舞片,曾经被认为无脑。
我还记得,很多和我同辈的人当年嫌弃德米的电影,尤其是《柳媚花娇》。“他用力过猛了,”我的一个朋友评论。
有些人对达米恩·查泽雷也有相同的评价。但也许几十年后,大家会很喜欢《爱乐之城》。
《柳媚花娇》(1967)
无论如何,我并不想批评这部有趣又有野心的电影。我更感兴趣的是《爱乐之城》是如何结合了制作厂歌舞片与德米的手法。我也想寻找它和百老汇秀(第三种歌舞片传统)之间的联系。
沿着这三个方面,我希望借什克洛夫斯基所言,追问电影技艺。《爱乐之城》既是沿袭又有创新。其实,大多数电影都是如此,只是占比不一。
歌曲情节
如果想了解电影形式和风格如何奏效,我们不能忽略电影制作的基本要素。为了达到某种效果,电影工作者们创造了电影手法的惯例,各种由松散的规定界定的有益的方式组成。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惯例的建立出于本能,就觉得这个方案可行。总之,在这些被偏爱的表现手法背后,我们可以找到值得挖掘出来的设计概念和呈现方式。从70年代起,我和克里斯汀·汤普森就想揭示电影制作人们背后使用的习惯和常用手法。这些都帮助塑造着观众如何理解电影。
我们不是执着于进行系统化的分类——艺术是不能完全地被系统化的——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们想辨别故事与风格的固定模式。而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想了解故事和风格的规律是如何从早期电影中一代代传承到当代导演手中的。
比如,一部分的美国制作厂电影的叙述模式是我在《重新发明好莱坞:40年代的导演如何改变了电影叙事》一书中想探讨的。在不说太多电影理论的前提下,我想说明的是叙事的技艺传统在那个关键的年代如何被重新定义的。
我最近的一篇评论(《波德维尔谈2016年的一些新片》的那篇文章)就想体现当年的电影遗产如何在现今电影中重现,包括《爱乐之城》。
其他的学者也在做技艺方面的研究,并不仅仅是电影领域。艺术史学家、音乐学家已经做了很多年的相关研究。在剧场美学领域,杰克·菲特尔新近出版的《美国音乐剧的秘密生活》令人激动。
书的副标题《百老汇秀是如何制作的》是致敬(我猜是无意之举)什克洛夫斯基的论文《⟨堂吉诃德⟩是如何完成的》。不过,目的都是一样的:仔细地研究艺术作品,展现制作过程的一些基本原则,同时也公正地评判它对于其继承传统的改进。
菲特尔提出的一点是“歌曲情节”,也就是一系列已成为百老汇固定传统的音乐剧歌曲。当然,很多曲目是为了增强剧情的戏剧性,但有时它们也表现情绪的变化或是情感的爆发。歌曲情节不仅与情节相呼应,也有其自身变化而带来的乐趣,通过一些与主线剧情不直接相关的旋律为观众带来另一种享受。
菲特尔戏剧的解析有趣之处是,在不同的音乐剧中,即使是和主线剧情无关的旋律也常常出现在同一个位置,而且抒发同一种情绪。借电影研究里被用烂的话讲,它们并不只是“打断叙事的奇观”。
作为奇观,它们有自己的规律,带来一种剧情的享受之外的之外满足。也许很多内行人和音乐剧迷了解菲特尔说的的宏观模式,但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并帮助我理解《爱乐之城》的音乐特征。
所以才有了这一篇评论的标题,而且100%剧透。我将《爱乐之城》看作是一部依照经典构思的电影。我将用菲特尔的音乐剧模板来验证它的“诞生”。最后,我总结出一些结论,阐述为何分析这些模式能突出体现了该片对于其沿袭惯例的演变。
从相遇相知,重逢,到再重逢
首先是好莱坞情节结构。克里斯汀认为,虽然美国主流编剧有时声称自己遵从三幕剧的写法,但他们在实践中常常被迫写成四幕剧。具体来说,一个很长的第二幕,若以更有效地眼光来看,常被看作是被电影中点分开的单独两幕。
传统的剧情结构由四部分组成:
1. “设定”,主角明确他们的目标;
2. “情节复杂化”,主角的目标被重新定义;
3. “发展”,目标被干扰、推迟、加强;
4. “高潮”,解决目标。
每个部分一般是20到30分钟。不论时间长短,电影可以包含比这四部分更多或更少的内容。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有一个尾声。
《爱乐之城》差不多正好是120分钟,如果不算片头的公司商标和片尾字幕。“设定”部分(25分钟),米娅和塞巴斯汀这对双主角都被交通堵在了路上。
然后,我们跟随米娅经历她的一天,看到她在咖啡店当服务员、试镜失败、回到公寓、同意和室友一起去一个社交派对。
然后闪回到堵车的场景,这次我们跟着塞巴斯汀回到他的公寓。与米娅的一天相似,他在家里煮咖啡,翻找欠费账单,和姐姐聊天。之后,他去工作,在鸡尾酒吧弹圣诞歌曲的钢琴师。米娅恰好走进酒吧,站在他面前,被他的即兴爵士感动。但塞巴斯汀被炒了,很不满,冷漠地撞到了她,就离开了。
“情节复杂化”在米娅再次试镜失败后开始。她去了泳池派对,看到塞巴斯汀在乐队里表演。她戏弄了他,之后两人一起离开了派对。虽然他们之间有点小摩擦,但一段友谊开始了。他们流露了自己的梦想:她想成为演员,他想开表演经典爵士的酒吧。
米娅无意中答应某天晚上和他一起看电影,但是忘记当天和男友有约会。不过,她无法忘记塞巴斯汀的音乐,后来在电影院发现他在看《无因的反叛》。他们去了在电影中出现的天文馆,然后接吻。在“情节复杂化”部分的结尾,大约全片60分钟处,米娅决定要为自己写一出女性独角戏。
“发展”则是一种延伸:介绍背景故事,阻碍造成了推迟,次要情节与主线交织起来。因为在《爱乐之城》中,爱情故事看上去比较稳定(没有情敌),而且也没有重要的配角。本片重点在于另一条主线:这对情侣追求成功时遇到的阻碍。而这些阻碍反过来影响了他们的感情。
“发展”往往也依赖于蒙太奇,片中大量运用了这个手法。米娅准备她的独角戏,而塞巴斯汀受到了邀请加入他的朋友基斯的小型爵士乐队。为了让他与米娅有稳定的生活,他接下了这份工作。
他开始巡演,乐队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虽然他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你喜欢你弹的音乐么?”米娅问他。他闪烁其词。当他因为乐队要拍照,而错过了米娅的惨烈的首次演出, 危机来临。
米娅宣布,“结束了”—意味着她的前途和他俩的关系。她回家了。这时候电影过去了90分钟。
我们准备好迎接高潮,它往往有一个时限。塞巴斯汀接了一个邀请米娅参加试镜的电话。他催促她回来。她拿到了角色。两人决定等待,看看他们的感情会如何发展。
五年后,米娅如今是个成功的演员。这看上去很突然的,甚至是反高潮的,因为这仅仅发生在“高潮”部分开始的11分钟后。显然,虽然他们说了会一直爱对方,但他们的关系没有再继续。
我们看到米娅去了以前工作过的咖啡店,回到丈夫和女儿身边。她的情景和塞巴斯汀独自在公寓的场景相互交错。在效果上,这一段平衡了开头“设定”部分他俩的交替的登场。
米娅和她丈夫去了酒吧,结果发现是塞巴斯汀的。米娅和塞巴斯汀渴望地看着对方。米娅看着他弹奏属于他们的歌。而由歌开始了一段他们共同的幻想,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发生的高潮与结局。
这一段重现了他们在鸡尾酒吧的相遇,但这一次塞巴斯汀没有碰撞她离开。他们热吻。在这“如果当初”的前提下,他们跑去试镜,跑去试镜的场景用了风格化的形式呈现。
接着展开米娅的职业生涯——去巴黎,获得银幕成就,建立家庭——这一次,塞巴斯汀是她的伴侣。影片的最后,和她一起坐在酒吧的是塞巴斯汀(实际上听着自己弹的音乐),而不是她丈夫,然后他们接吻。
一组甜蜜的闪回与幻想以传统的浪漫拥抱结束。但电影的尾声则是他们回归现实,当她与丈夫离开时两人脸上都挂着苦笑。总的来说,双高潮/结局大概是30分钟,对于非歌舞剧来说是很长的。
按好莱坞叙事电影的习惯,主旨与平行叙事在电影中交错出现。片头高速路的歌曲已经暗示着之后的发展。这首歌男女交替,女声唱追求电影明星的事业(“它呼唤我上大银幕”),男声唱着要荣耀经典音乐的事业追求(“酒吧里的歌谣是曾经光顾此处的人留下的”)。而女声部分结束时提到了一个男生在银幕上看到她并记起了她,预示了电影的结局。
之后是更多的平行与呼应。米娅差一点就在约会时放塞巴斯汀鸽子;而他错过了她的演出。他们都鼓励对方继续奋斗。米娅的蠢男友预示了她最后会找《GQ》杂志中会出现的丈夫,好像她决定不要再找像塞巴斯汀一样的急躁的男人。
米娅敬爱的阿姨曾激起她对电影的热爱与对表演的渴望。阿姨的主题在电影中戏剧性地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她的女性独角戏,一次是她试镜演唱中更为成功地展现,《献给有梦想的人》让她获得了这个电影角色。
电影中许多情节都是被双倍呈现的,所以并不奇怪,在开头“设定”部分的平行结构将他俩的一天平行处理,并奠定了在晚餐酒吧的重要一刻。而那一幕也被重复演绎了—一次在真实世界,当她和她丈夫听到塞巴斯汀为演奏她作的曲子;另一次是在幻想未来的开始,重现了她与她丈夫的现实生活。
到此为止,都太经典了。但正如他们所说,《爱乐之城》同时也是音乐剧。
这是百老汇音乐
我对《爱乐之城》的情节发展概述是比较空泛的,可以扩展成更细致地分析每个时刻的冲突与改变,或是联系角色,分析他或她经历的信息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电影制作的另一层——将它看作是音乐剧—更具体地说,是百老汇音乐剧(难怪作词者都有舞台背景)。菲特尔的理论帮了我很多。他的歌曲情节原型模式相当契合《爱乐之城》,而其中相异的地方也很有趣。
黄金时代(1942年—1975年)的百老汇音乐剧总是和好莱坞电影一样有双线情节的特性。音乐剧和电影都会将爱情线设为主线,而这让剧情与歌曲情节相互融合。
就像在很多电影中一样,百老汇音乐剧中,主角情侣们想在感情和工作上都找到快乐。目标相互联系,是推动动作情节发展的核心动力,而且目标也成了歌曲情节的有机构成。
导演达米安·查泽雷显然对以高速堵塞的歌曲开篇有些迟疑,但他和剪辑师汤姆·克洛斯很快就决定电影即刻确定影片歌舞片的基调。我认为,演艺圈传统的压力起到了作用。根据菲特尔所说,典型的音乐剧会以个人独唱开始,比如《奥克拉荷马!》的《哦,多美的早晨》。
但也可以以“盛大的舞会”开始,比如说《爱乐之城》的《又一个晴天》自然属此类。它以一种类似和戴蒙·拉尼恩的《红男绿女》活泼开场的方式,交待了社会背景与基调,。它同时也表明了演艺圈成功的核心目标。
菲特尔认为第二首歌极为重要。这是一种表明“我想要什么”的歌,是第一次展现主角的目标。在《爱乐之城》中,这首歌是《人群中的某人》,以打扮美艳的室友合唱开始、米娅的独唱结束。那时,她寻找的“某人”不仅是促进她事业的约会对象,而是她倾心的另一半。
当剧情进入“情剧复杂化”的阶段,米娅和塞巴斯汀再次在泳池派对邂逅。他在一个无趣的复古乐队演奏,而她捉弄他,算是为那次他在钢琴酒吧拒绝自己报了仇。接下来是歌曲情节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菲特尔所说的“有条件的情歌”。
比较典型的是《天上人间》的《如果我爱你》。这首歌表明了男女主在一起不合适。它起到的作用是阻碍、推迟感情线。在非音乐的爱情喜剧中,则是以口角、争执与竞争体现(比如《电子情书》)。
显然,《愉快的夜晚》是一首有条件的情歌,因为米娅和塞巴斯汀都说洛杉矶的景色对于相爱的人来说才是完美的。但是,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虽然言语上拒绝了情感的发展,音乐和舞蹈都表明他俩应该在一起。
菲特尔认为,歌曲情节发展到这步需要一阵情感的爆发。他称之为“噪音”。在《爱乐之城》中, “噪音”来自于爵士酒吧的乐器表演,在电影原声中叫做《赫尔曼的习惯》(译者注:赫尔曼是美国爵士大师)。
这旋律在叙事上并不是毫无作用的,这是一个展现塞巴斯汀所热爱的古典爵士乐的令人陶醉的集体创造力的音频母带。而且,也表现了米娅对塞巴斯汀好感增加,也相信他的梦想。
但至此,菲特尔的百老汇原型与《爱乐之城》偏离,它指向一个电影关键点。传统的歌曲情节中往往会有一首曲子是关于第二对情侣或是次线情节。想想《睡衣仙舞》中的那对搞笑的情侣和他们的歌《我再也不嫉妒了》,表现了海恩斯对于失去格拉迪斯不合理的担忧。
这音乐剧也有一条与狡猾的哈斯勒进行的劳动谈判的次线。但是《爱乐之城》没有关于另一对情侣、三角恋或是反派人物的次线。所以也没有相应的歌曲。
按照菲特尔总结的模式,接下来是主角主题,一个为主要演员设计的特殊曲目,当Sebastian在码头自我反思时,歌曲“繁星之城(city of stars)”就完成了这一使命。
菲特尔认为,接下来音乐应开始增强、累积能量,直至第一幕闭幕。当两位主人公在格里菲斯天文台第一次约会时,音乐“双人舞(pas de deux)“ 就起到了这一作用。
进入情节的“发展“阶段:Mia忙着她的独角戏,Sebastian随朋友的乐队巡演。有多首音乐出现在了那组夏日蒙太奇情节中,包括Sebastian和爵士组合的表演、情侣在钢琴前对唱的那段“繁星之城(city of stars)”。
这组音乐不太符合菲特尔模型,不过作为幕歌,the messengers乐队所演奏的电影主题曲“start a fire”倒是很契合。这场音乐会上淋漓尽致的表演,让Mia开始隐隐有些担忧。
鉴于菲特尔的观点,第一幕的结束往往预示着希望的破碎,因此,我认为影片中演员的表演应与“幕歌”(“curtainsong”)的这一功能相符。在《吉卜赛》(“Gypsy”),《红男绿女》(“Guys and Dolls”),《旋转木马》(“Carousel”),《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等音乐剧中,“幕歌”(“curtainsong”)都宣告了主人公目标的失败。
菲特尔认为,“典型的第一幕”是“每个人计划中的事于瞬间破产”。影片中那场音乐会并没有这么强烈,但Sebastian在乐队疯狂演奏R&B的时候稍稍调整键盘,也表明了他在背叛自己。“你演奏的音乐是你所爱的吗?”他似乎放弃了自己的梦想,追梦的失败成为两人关系的第一道裂痕。
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有一些相对独立的曲目,但也缺少了菲特尔模型中的几首功能性曲目(表达回归的歌曲, 第二个主角主题曲, 一次盛大的歌舞展示以及一些配合副线情节的曲目)。欧文·格利伯曼指出,进入第二小时后,电影明显缺乏活力,高潮中第一个情感充沛的曲目也是忧郁的。
与Mia那场较早的、过度渲染的面试相反,歌曲“追梦的傻瓜(The Fools Who Dream)”更像一首轻柔的自白。这正符合菲特尔所说的“第二幕展示(second-act showpiece)”,并且正如这一传统所要求的,它导致了一个重要的情节转折点:Mia拿到了那个角色。
这段情节的结局,也就是菲特尔所称的“倒数第二幕(next-to-last scene)”,则完全不需要以歌舞的形式呈现。它往往是一个“书面场景(book scene)”,在本片中的相应情节是:Mia拿到角色后,她和Sebastian都承认了他们对彼此的爱以及在一起将面临的困难。
随后是尾声,与开场高速公路的场景呼应。如菲特尔所言的“午夜前的一幕(The 11:00 scene)”往往是一次大范围的重演。《爱乐之城》这八分钟的系列场景,既展示了音乐的主题,也表现了幻想中另一版本的Mia的事业人生。
《俄克拉荷马》以那段广受欢迎的梦幻芭蕾著称,在《锦城春色》(“On the Town”)的白日梦桥段(“Miss Turnstiles”)、《蓬车队》(“The Band Wagon”)中挑逗女孩的桥段以及许多好莱坞影片的“如果”情节设计中,这一歌舞传统都得以体现。《爱乐之:?城》的新奇之处则在于将这段梦幻巴黎保留到最后,使幻想与真实形成对照,结局苦乐参半。
《爱乐之城》的创作过程说明,电影人总是不断权衡插入歌舞片段的时机。本片最终选择了经典百老汇的布局模式,说明菲特尔提出的“歌舞情节”(“song plot”)有其自身优势,创作者们直觉性地被它吸引。这一模式的情绪弧线完善并延展了故事本身的情节。
所长与所短
菲特尔对百老汇“歌舞情节”的剖析补足了古典剧作的技法。它帮助我们理解创作者们心照不宣的指导原则,也展现了那些并非来自歌舞剧舞台的影片是如何吸取歌舞剧传统的。菲特尔的布局模型不仅指出了《爱乐之城》和音乐剧的密切关系,也让我们看到这部影片与传统程式相悖之处。
《爱乐之城》省去了三角关系、副线情节、反面人物和“次要情侣”。Sebastian的姐姐承担的是解说功能,Mia的室友们则缺少角色的性格塑造,Mia的父母也很少出场。乐队队长Keith很大程度上只代表音乐发声,其他乐队成员则没有被赋予人物个性。完全没有次要人物来打断精彩的表演。
影片牺牲了副线情节,相应地就丧失了情绪氛围的多样性、主旨的两面性以及喜剧成分的调剂作用,两个主人公频繁纠缠的恋人关系缺乏调剂。
本片放弃了副线情节所带来的愉悦感,例如《红男绿女》中那唐·底特律(Nathan Detroit)和阿德莱德(Miss Adelaide)的浪漫关系,又如《在圣路易斯遇见我》(“Meet Me in St. Louis”)中父母在钢琴前演奏的情歌。
可以说,《爱乐之城》也不得不面对改革传统所带来的弊端。
《红男绿女》(1955)
奇怪的是,如此简化情节却支撑起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叙事。
《封面女郎》(“Cover Girl”),另一个讲述演艺圈故事的好莱坞影片,比《爱乐之城》要短15分钟,却有充分的时间对次要人物进行全面呈现:与罗斯蒂(Rusty)竞争女主角的对手,为伊芙·阿登(Eve Arden)量身打造的出彩角色,关于罗斯蒂祖母的平行叙事(通过闪回呈现)等。
《封面女郎》(1944)
在第95分钟,《锦城春色》插入了三对情侣和一个纽约旅游节目。至于经常被援引的德米的作品,其中时长90分钟的《瑟堡的雨伞》(Umbrellas of Cherbourg),设法用两个年迈的女人、两个巧妙独特的情敌来丰富情节。
《柳媚花娇》(Les Demoiselles de Rochefort)则是更好的体现,虽然同样时长两小时,但它包含了五对情侣,一组三角关系,一个一心想当明星却被封为连续剧杀手的咖啡店服务生。
此外,《爱乐之城》没有赋予主人公清晰的目标。他们只是想成功,一个通过海量的演员面试,一个通过一场场的音乐演出。在《封面女郎》中,罗斯蒂面临的一个个抉择都十分清晰:签约成为模特或继续做酒吧舞女,嫁给键盘手或百老汇制作人。
正如菲特尔指出的,《俄克拉荷马》中还有“州”这一更大的议题,《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中有关于国家现代化的议题,《在圣路易斯遇见我》中有整个家庭从圣路易斯搬迁到纽约的议题。而《爱乐之城》则相对封闭地在一对情侣之间来回往复。
《俄克拉荷马》(1955)
那么,是什么填充了《爱乐之城》两小时的时间呢?
一方面,是先前提到的平行结构,尤其是咖啡店里场景的拓展,此外还包括泳池派对那一场对电影工业的旁敲侧击以及天文台中那段优美的舞蹈。
在更早的大片厂时期,影片中浪漫关系会发展得更快,在影片“建构”阶段,角色将面临更犀利的抉择,朋友、家人和一些同样出彩的配角使主人公的生活环境有血有肉。(比如本片中,Keith可以被塑造为一个情感助手,最好是一个爱说俏皮话的人。)德米的电影也会按几何对称原则加入更多的角色。整部影片都会更加多姿多彩。
单薄的情节可能使这部影片为人诟病,但如此集中于一对情侣的音乐剧也许值得试验。但从个人口味来说,我喜欢这部电影,我看到其中诸多不易且有价值的努力。
但更重要的是它引发我对于制作传统的思考,特别是当它们影响剧情结构的时候,从对制作方法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爱乐之城》既是传统的又是革新的。电影的演化很重要,但也许应该由深入的分析引航。电影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影片的制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