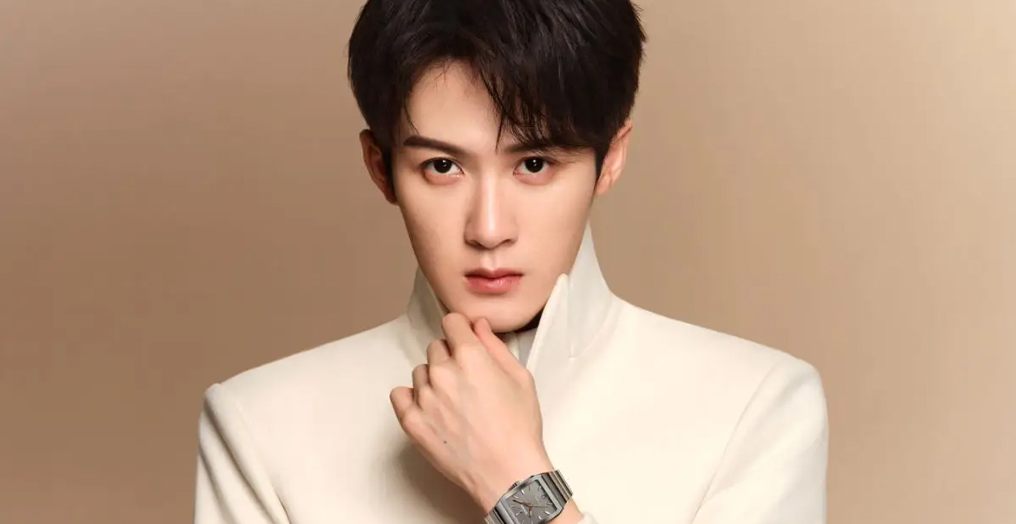动荡的时代背景、惊心的黑帮谍战、民国风情与西洋元素、礼帽长褂,红唇旗袍。
《罗曼蒂克消亡史》,这部电影有着一个充满法式优雅的名字,高格调手法与史诗式叙事集齐了影迷的所有偏爱又不失导演的个人情怀。

近些年,有才华的新锐导演虽然稀缺,劲头却着实凶猛,思维活泛和勇于尝试是最大的优势,毕赣的《路边野餐》、翁子光的《踏雪寻梅》、韩延的《滚蛋吧!肿瘤君》的口碑普遍都比较好,程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在今年12月16日圣诞档上映,票房虽不及同期上映的《长城》,但口碑不错,豆瓣评分达到7.6,关注热度也是从15日开始不断攀升。


▲《罗曼蒂克消亡史》百度指数
口碑好说明大部分人对这部电影是肯定的,看不看得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外来词组成的隐晦片名、跳跃式剪辑、时空的倒错让无数手拿爆米花的观众“智商沦陷”,很多地方并没有看懂。其实在结构上“玩儿花样”是导演程耳一直以来的“怪癖”,他在《边境风云》中设置大量留白和反转,将故事发展的大部分可能性留给了观众,《第三个人》里又采用戏剧式的镜头片段,到《罗曼蒂克》里的碎片化叙事,程耳说自己喜欢从中间开始讲故事。

这样结构电影就像拼图游戏,所到之处埋尽悬念,真相和彩蛋也许到最后一刻都无法完整地呈现,观众可以收集这些片段来组接,顺便完成了与导演的互动,就像程耳自己说的:“让观众自由的连接”。
将打碎的片段按照时间顺序重组,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
1934年,电影明星吴小姐出演了《花好月圆》。而在戏外,其丈夫(吕行饰)跟卢师长的三姨太在一起时被发现。为救丈夫,她向陆先生求助,陆先生帮她体面地解决了此事,并把她引荐给更高权势的戴先生。
同年,陆先生答应王先生太太小六出演《花好月圆》,以求让花心的她安分点。小六又跟电影男主角赵先生幽会,被要求离开上海。陆先生的妹夫渡部将她送往苏州,在途中杀死了同行者并强奸小六,把她带餐馆囚禁成为性奴。其间,王妈引荐了一个身手了得的车夫做陆先生的贴身侍卫。
1937年,淞沪战役前夕,陆先生出面跟周先生谈判,解决了罢工事件。日本为进一步瓦解上海,企图跟黑帮大哥王老板、老二张先生以及陆先生谈银行合作。日方察觉陆先生有意打消张跟他们合作的意向,于是计划把陆先生杀死,并与身为间谍的妹夫渡部勾结,结果陆的家人全部被杀。
1941年,陆先生在香港通过报纸看到了张先生跟日方合作成立银行的新闻,于是委托远在上海的老五和车夫,杀掉当年背叛的老二。同年香港沦陷,戴先生委托陆先生照顾吴小姐一起逃到重庆。
抗战结束前夕,陆先生来到上海收容所找到被囚禁的小六,并与她一起前往吕宋岛。佯装成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车夫,当面杀死了渡部的大儿子,小六同时举枪击毙渡部,之后不知所踪。
1949年,陆先生独自一人去了香港,从此销声匿迹。
《罗曼蒂克》是“作者电影”的代表,程耳自编自导自剪,实现了一个消亡和一个建构。
罗曼蒂克的消亡
《罗曼蒂克消亡史》其实就是字面意思:浪漫的消亡史,而这个片名中又有着更深层次的所指。整部片子始终在点题,我们能看到美好的人和事随着时局的变迁分崩离析,构成一段由盛转衰的历史。
历史是框架,美好的人和事是血肉。角色的典型化设置浓缩了战乱中的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是一个群体,于是小人物被放置在大历史中,被赋予了沉重的时代枷锁,战争击垮了他们的生活也摧毁了这个时代,帮派大佬四散奔逃,小六杀死渡步后不知所踪,吴小姐被丈夫抛弃,处男遇上妓女,老五帮助陆先生杀死投靠日本军方的张先生。战火纷争,繁华尽落,罗曼蒂克消亡,还有被浪费的时光。

陆先生风生水起到家破人亡
陆先生是上海叱咤风云的黑帮大佬,举止儒雅、心狠手辣、遇事从容、有仇必报,与王先生和张先生是拜把兄弟,还有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儿子。一家人经常其乐融融聚在一起吃饭说笑打麻将。虽是黑道人物却忠于国家大义,面对日方合作开办银行的要求断然拒绝,于是他的日本间谍妹夫渡部与恼羞成怒的日方合伙杀了陆先生全家并佯装中弹使陆永远不会怀疑并替他抚养两个儿子,而渡部自己则三年前就将陆先生中意的交际花小六强奸并囚作性奴。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陆先生遇见了沦为慰安妇的小六才真相大白,在杀死渡部之后陆先生独自一人去往香港,后续不明。

小六花心阔太到沦为性奴
陆先生的“大哥”王先生为了娶小六休了前妻,陆先生对她同样有好感,但是拥有一身美艳皮囊的小六内心却并不安分,毫不忌惮地勾搭喜欢的男人,甚至被抓到与大影星张先生偷情也能被给足盘缠遣往苏州,也算是活得春风得意。而这一切的消亡也就此开始,渡部受陆先生委托送小六去苏州,一时兴起强奸了她,把她囚禁在自己的餐馆里作为性奴长达四年,后来渡部去参军,不忍心杀死她,战乱中,小六沦为日军的慰安妇。战争胜利在陆先生的帮助下杀掉渡部之后不知所踪。

吴小姐与丈夫相互依偎到冷血背叛
吴小姐是战时民国人气很高的大影星,丈夫跟着一起拍戏,对自己言听计从,两人在纷乱中彼此依靠。但是丈夫的演技并不高,在吴小姐的光环下逐渐疲惫,与某位姨太太幽会之后被抓,吴小姐求戴先生帮自己救出丈夫却为戴先生中意,拒绝的过程中得知她的丈夫已经同意以吴小姐搬进戴府为条件获得了一份安全的肥差。

王妈和老五忠诚陨落
陆府的大管家王妈和姨太太老五自始至终忠诚于陆先生。王妈在中弹死去之前不忘最后给陆先生写一封信,老五执意要和车夫一起枪杀二哥张先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她们代表忠诚,死亡的结局象征着美好德行的消亡和陨落。

这一切的美好终于战争带来的恶,程耳在其中埋藏着很深的象征意味,罗曼蒂克消亡的一方已经面目全非,而造成罗曼蒂克消亡的一方,也没有好的下场,整部电影落得一地鸡毛,看起来是万恶之源的渡部到头来沦为战服,死在小六手下,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知著君觉得,《罗曼蒂克》里没有坏人,有的只是特殊历史时期下异化、畸形的人事,罪魁祸首是更强大的力量,小人物在社会变迁的洪流中被动前行与自保,显得无力又无奈。
导演个人风格的建构
程耳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科班出身,当时在班里就比较“有才”,曾“自诩”自己的文字比电影要好,17年只拍了4部电影,从毕业作品《犯罪分子》开始,他就在模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新的影像可能,一步步地摸索到《罗曼蒂克》达到一个高峰,从编到剪亲自操刀,复杂精巧的结构需要格外严谨的剪辑逻辑,程耳磨了一年多,花了不少功夫,可以看到野心已不只于票房和认可度,更多的是在作风格化的努力。

从《罗曼蒂克》中知著君看到了两个关键词:对称和失衡。矛盾的存在,就像影片所描述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一样充满对立与冲突。
1对称 中轴线构图
电影中大部分镜头固定且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中轴线两边是一样“重”的构图比例,有观众感觉像在看《布达佩斯大饭店》。

程耳解释说:“我一直偏爱对称,无论是叙事还是构图,都讲究对称,这更多的是一种本能。”
他还说过《罗曼蒂克》里没有多余的道具,王妈给吴小姐带话这个场景,两人被桌上的糕点纸袋隔开,也能因此感觉出两人之间是隔着事儿的,吴小姐对王妈并不是完全信任,并且“嗅”到了坏消息的气味。

小六与张先生偷情之后与陆先生坐在一起对话的镜头同样采用这种方式,将人物用窗帘和墙隔开,陆先生背后是一片阴暗,象征着森严的规矩,小六身后是窗,又像牢笼,代表着自由预示着囚禁。

“三段式”叙事的首尾呼应
导演虽然打散了故事片段,但是大体的结构还是对称完整的“三段式”+首尾呼应。电影中首先从中间讲故事,交代陆先生平息罢工和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这两件事,一方面告诉观众张先生有合作的意向,为文末做铺垫,另一方面强化陆先生的人物性格与形象。

然后从王妈被杀开始,将陆家全家被杀的结果全盘托出;第二部分则回到故事的最开始,也就是1937年,从陆先生答应让小六出演《花好月圆》开始,直到张先生与日军的银行落成,到第三部分,陆先生派车夫杀了张先生,1945年的重庆,吴小姐对陆提到:“大概是喜欢那个地方,就会喜哪里的菜。”让陆先生想到渡部的日本餐馆,恍然大悟,这时候,导演开始呈现真相,解释呼应了片头陆家被灭门的桥段。

重复画面与配乐的运用
重复的画面与配乐同样被分别放在首位。整部片子的第一个镜头是在渡部的餐馆,而第三部的第一个镜头在相同的位置,用相同的景别和构图,甚至人物的站位和动作差别都不大,同样是摘掉礼帽,脱去长袍,而摘礼帽的动作在全片最后一个场景中有出现,带有明显的仪式性,那便是罗曼蒂克消亡的喻指。

第一部分陆先生的儿子被杀与第三部分渡部的儿子被杀之后的段落都紧跟《你在何处,我的父》这首插曲,迫使观众将两个场景联系在一起,产生惩罚恶者的情绪快感,达到了重要桥段的前后呼应,并不仅仅塑造陆与渡的对立,还通过音乐将他们一致化,一同抽离出来,一起作为大环境的牺牲者。
2失衡 人物行为与身份的错位展示
通过发散形的网状人物关系线,我们可以被简练的叙事震撼,因为撑起大小事件的人物是“圆”的,复杂多样甚至表里不一。

程耳在《罗曼蒂克》中的人物塑造极力向真实靠拢,不仅仅是生活层面的真实,还是更高层次的本质上的真实,挖掘人性的美好和虚伪。这组两极化的词可以自然地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这种两级可能都是你,就像现实中的你我他,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展现的自我也是不一样的,也可能都不是你,那就需要老到的演技和逼真的面具了。衣冠禽兽渡部,温文尔雅的黑帮大佬陆先生,包括柔弱任性的交际花小六,在黑暗痛苦的日子里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坚韧都是人物行为与身份的错位,涵盖时代的烙印,传递给观众的便是真实和精彩。

罪恶的极端暴露
《罗曼蒂克》的片名、格调、配乐都透着一股西方气质,甚至加入了天主教元素来描述罪恶。七罪宗,是天主教教义中七种罪过的来源。教义中提出“按若望格西安和教宗格里高利一世分辨出教徒常遇到的重大恶行”,这些恶行会引发其他罪行。愤怒、贪婪、暴食与色欲四大罪宗在电影里被展示得淋漓尽致,人们吃饭、做爱、抢夺、意淫、屠杀,积聚到片末,渡部完全占有了小六,吃饭与做爱不停地重复到最后开始残杀,两人逐渐化为一种符号,他们所做的事凝集了片中所有的色欲、暴食、贪婪与愤怒。

导演丝毫不避讳人类最本能的原罪,将人性的“本我”裸露,放大,聚光,赤裸的原罪与道德伦理激烈地冲突,心灵唯有遭受撞击才能得到升华。两段插曲《你在何处,我父》,升格镜头俯拍暴戾后的一片狼藉,天父之眼,冷峻悲悯,空灵的诗,祈祷回归圣洁。程耳用疏离感和音乐构筑了属于自己的“暴力美学”。

理性的冷峻史诗与感性的情爱纠葛
战乱大背景、固定镜头、人物正面的近景。家国大义、爱恨情仇、命运悲剧。《罗曼蒂克》用节制的动作一点一点积聚着压抑的情感,理性与感性看似对峙实则是互相增益的,无声的呐喊往往用来表达最强烈的控诉。片中的镜头与演员都是克制的,镜头少有移动镜头,演员收敛肢体。无情背叛,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这么安静地演过去,观众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非常规构图
这部戏中,程耳常常会尝试陌生化构图。

将人物设置在画框边缘

极仰与极俯


正面近景的重复使用


给不寻常的人事一个不寻常的视点,是对镜头语言的探索,同时也是在失衡中建立自己的影像风格
上帝视角与微观全景
俯拍的上帝视角与黑猫的微观视角也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失衡处理。观众既能宏观纵览也能关注细节。上帝视角带来恢弘和庄严,黑猫经常出现在渡部的餐馆中,知晓一切虚伪和肮脏,象征着无处不在的罪孽,那就是人类无法逃脱的恶的根源。

古典视觉与西洋配乐
古典与西洋元素的搭配运用的十分巧妙、契合,程耳认为当时的上海已经出现西方的音乐,人们的生活中也出现了西式的印记,《海上花》、《胭脂扣》、《滚滚红尘》等电影中民国时期的上海形象已经固化,程耳的野心不允许自己在框架下拍电影,他要“任性”地另辟一条新路,于是电影配乐的器乐部分基本为西洋古典音乐,选用了数段舒伯特的乐曲并加以改编,梅林茂与郭思达作曲的《Take me to Shanghai》、福音配乐《where are you,father》混合着民国装饰和上海话,反而使得电影呈现出新颖奇魅的高贵质感。


《罗曼蒂克消亡史》是一部任性的电影,有着青年导演渗透在其中的些许“锐气”,不仅将故事拦腰截断,从中间开始叙事,还叠加陌生化表现形式,并且不忘借吴小姐之口调侃自己:“我请教过导演,导演没准备让大家看懂,导演的意思,这是一部艺术片,是艺术,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一语双关的黑色幽默好不容易为“端着”的《消亡史》增添一丝俏皮又总是带点戏谑与嘲讽的意思。不过呢,知著君相信也正是这种出挑的性格才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影世界里一把抓住你吧。